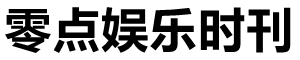本篇文章7471字,读完约19分钟
在1923年8月出版的第二十期《薛恒》中,发表了陈寅恪的《与妹妹的书》(节选)。全文如下:
我以前看过一份中国报纸的供状,商务印书馆重印了一本日文版的《大藏经》出售,预约券的价格大约是四五百元。恐怕有一天会不容易买到,即使有,价格也会更贵。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借一笔钱买这本书。因为我现在需要很多书,总价大约是10000元。最重要的是两个西藏郑文收藏,日本印度中国收藏,和其他零星的字典和数百本西方书籍。如果你不能,你就不能学习。我已经出国很长时间了,其中一半人在国外图书馆有这本书。一旦我回到中国,我就不能再研究它了,我将放弃我最初的研究。现在我真的想筹集一大笔钱来买书,然后我就回家。此时如何获取该段落?这只能被认为是of/きだよ 0。是不是很可怜?前年,我给甘肃宁夏的道银写了一封信,请他买一套藏画。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实现。也就是说,它太贵了,所以我知道我很穷,我不付现金,我拒绝支付。藏经,许多龙树和Aśvaghoṣa的作品,还没有在中国翻译。也就是说,译者也可以比较异同。我今天对学习藏语很感兴趣,因为藏语和汉语属于同一种语言。例如,梵语与希腊、拉丁语和英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同属一个家族。因此,音韵训诂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因为藏语几千年来都是用梵语字母拼写的,所以它的变化比汉语中的变化更明显。如果把西方语言科学作为汉语和藏语的比较研究,结果应该会越来越好。然而,这不是我的注意。我注意到两件事:一是历史(唐史,西夏),西藏是吐蕃,藏汉关系不言而喻。佛教和大乘经典在印度很少见,在新疆出土的也是零星的。和Hinayana vinaya等。,这与佛教的历史有关。中文翻译,相当难懂。我已经检查了金刚经。从晋唐到虞屈原,有数百种注释,但我不知道有多少误解。我想,除了印度和西域的外国人,中国的金代和唐朝的僧侣也能理解梵语,当他们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看着经文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够好。隋朝智者天台宗之父对“四大谈”一词的解释错得离谱。幸运的是,唐太宗是儒家五经正义的两个疏体,不管它是否谈论佛经,这是一个佛教禅宗自己的学校,与印度无关。(禅宗说它是由叶佳传达的,它是基于“法律保护的命运”。现在这本书被证明是伪造的。我怀疑达摩说的话。)老西藏一时半会儿得不到。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但我听不见。还有蒙古,满洲,回文件,我要。你可以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如果北京有满文、蒙古文、回族和藏文文件,如果价格低,请大哥和五哥给我买。过了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将会很少见。

(收录于《金明博物馆藏》第二版,以下简称第二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312页。(
第20期《薛恒》
这是陈寅恪在柏林求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首先,信中说,回国前,他必须准备两个连续版本的藏文,两个连续版本的中文,大约100种西方文件和其他零星的字典。最后,还有满语、蒙古语、回族和藏语的书籍,这些都是必需的。回国后没有这些材料,就没有办法学习。第二,我说我在学习藏语,我希望用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和藏语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我就可以超越甘佳的老人。最后,我说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其次是“唐史和西夏”。这里的“西夏”应该是“西藏”的错位,因为据说“西藏是吐蕃,藏汉关系不用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研究过西夏历史;另一个是佛教,其中大乘经典和小乘律是最有价值的,但他“认为除了印度和西域的外国人以外,中国的金代和唐朝的僧人能懂梵语,当他们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时,其余的大多是找文学来生义,但缺乏道德。”同时,对《金刚经》的诠释以及天台宗和禅宗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当时,国内的学者还没有看到陈寅恪的真面目,读了这篇文章一定很震惊。此人不仅能读懂梵天、藏语、满语、蒙古语、回族等各种文字材料,还敢说中国人对佛教文献的理解,除了晋唐时期的僧人(指、玄奘、易经等老师)之外,大多是以看文献生义为基础的,这是完全不值得的。音调很棒,震耳欲聋。每次读《姐妹书》,我都想看看尹柯先生到底有多好,这让当时的学者们刮目相看。这篇文章发表在薛恒杂志上。主要负责编辑工作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是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朋友,可能只有吴宓能从家里拿到这样一封信来发表,信中有“节选”的标记,即只选了关于学术的部分。然而,这篇文章并不是当时在薛恒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章节。让我们来看看吴宓的年谱:1894-1925

(三联书店,1995年版)
很明显,根本没有提到这篇文章。然而,正是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吴宓向清华大学校长推荐陈寅恪的武器,使这位没有文凭却学业有成的留学生步入清华,与梁启超、王国维并列为四大导师。
陈寅恪在德国留学
1926年7月,陈寅恪到清华报到,开始了他在国学研究院的讲学和研究生涯。9月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宇,称:“陈三元最小的儿子已经到校。”此人研究过东方语言研究,他说欧洲学术界的情况非常详细。这篇演讲(伦顿)有一卷赞美中国摩尼教的文章,已经出版了。这卷非常相关。”

(《与萧来往书信札记》国伟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58页)
由此可见,即使是博学多才的王静安先生,也从初入欧洲学术界的陈寅恪那里听到了不少欧洲学术界的细节,其中有他所关心的摩尼教文献,即当时实际上并未发表的斯坦因的《下赞》(s . 2659)(1934年出版的日本《大正新修藏经》全文载于第50卷),但也有一些赞扬。例如,第1-82行,“赞一文淑”,第176-183行,“初声赞文”,第360-363行,“赞美日光之后”,第387-400行,“墨日听者的自白”,都是德国学者e .瓦尔德施密特(1897)写的

(" 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aismus ",abhandlung der(kniglich)-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哲学-历史学klasse,柏林,1926年,第1-131页。(
这篇长文章。当王国维听到这一点时,他一定觉得这“超越了我”。
在王国维看来,陈寅恪研究的是东方语言学。陈寅恪说,他想“用西方语言科学的方法对汉藏语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当时欧洲最成功的东方主义文献学。什么是语言学?北京大学的段青教授在《敦煌吐鲁番学》第12卷《德国印度学的开端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遗产》一文中对此作了解释

(季羡林先生纪念特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近年来,清华大学沈伟荣教授大力倡导文献学方法,出版了专著《回归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使我们对欧洲文献学的来龙去脉和学术方法有了深入的了解。关于陈寅恪先生早期的文献学研究,许多学者都有所论述,沈教授最近也有所论述。但是它们都是一般性的,而不是深入的。

1926年9月清华开学时,陈寅恪开始讲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文献学》,内容包括《摩尼教经典与维文翻译研究》、《佛教经典(梵文、巴厘文、藏文、维文和中亚文)各种版本的比较研究》等。这些显然是尹的。但教学不同于研究,它只是解释,因为观众没有基础,有些不会深入。让我们根据陈寅恪自己的著述来看一下他的“文献学”研究成果。

从1927年到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各种文本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有些比较容易理解。然而,西方学者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研究成果并不规范和统一,有时只提到书名,有时只用中文表述。读者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如果他们不知道所引用文献的学术价值,就无法理解尹克先生的贡献。作者系统地收集了西方人对中亚文字研究的目录,并多次开设“西胡语与西方文明”课程。我对尹柯先生引用的文献略知一二,以下是简短的答复。(出版社,尹柯先生在书名正文中没有标点符号,这是今天补充的。(

《大乘·赖斯的后记·钱景的疏听》(原载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研究论》,第一卷,第2期,1927年9月)。文章提到敦煌写本《法成》,“今知译著,……藏文包括藏文《郑文藏文善恶因果经》,易经《金光明百王经》的复译,以及观世音菩萨的三种法术(见《亚洲学刊》第11辑第4卷《石林》第8卷第1期《知那研究》等)。)”(《两个版本》,第254页,“享受”是“亨”的错误)这里提到的法国《亚洲杂志》,佩里奥特(p .佩里奥特),应该是《甘珠尔目录注释》(《康德尔目录注释》,亚洲杂志,第四期。法国中亚著名学者佩里奥特与中国学者交往甚多,也是陈寅恪的朋友,在此不必赘述。然而,日本的羽田恒和石屏俊达并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日语胡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梵文残卷:儿童遭受隐喻之苦》(1927年11月,中山大学语言与历史研究所学报,第1卷,第3期;同年12月,《清华学报》,第4卷,第2期):过去,德国人在龟兹以西,巴耶乌斯梵文中有许多佛教经典,由柏林路德维希大学教授亨利克·吕德斯教授核对。其中有一本《伟大的庄严理论》。尹柯尝过普鲁士的味道,教过东方古代文献学,所以他也听说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读完了所有的印刷书籍(布鲁克·斯特吕克尔·德·卡尔潘ā·曼迪提卡,她在莱比锡的奥格格本·冯·富莱德,1926)。专业精神在世界上是众所周知的,而这所学校尤其是最好的作品,任何能读懂它的人都知道它,所以它不值得称赞。本文仅将原梵文对作者姓名的考证,以及这一理论的原名称,与原汉译本进行比较,并举出几个例子来看鸠摩罗什的阐释艺术,这可能对那些看待古代佛教翻译史的人有所帮助。

(《第二卷》,第207页)
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勒德施教授现在通常由鲁德斯(1869-1943)翻译。他是当时德国东方学术界的领袖,也是国际中亚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和民俗调查协会德国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组建了“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由阿尔伯特·葛兰(1856-1935)率领,阿尔伯特·冯·勒·库格(1860-1930)带领他于1902-1903、1904-1905、1906-1907和1913-1914年四次赴新疆考古,在吐鲁番和焉耆·鲁德斯很快就致力于对新获得的西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11年,他出版了《佛教戏剧的剩余页》(bruch stü cke佛教徒,柏林,1911年)和《Aśvaghoṣa's戏剧< Sharifutsu章>》(das Sā ripurakarana,ein戏剧des asvaghosa),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1年,第388-411页。以下标题缩写为spaw)。尹柯先生提到的《大悲论》的发表,也是他整理龟兹出土梵文手稿的成果之一。鸠摩罗什是一个龟兹和尚,他可能同时写了这本书。十六国秦朝以后,他去长安翻译儒家经典。尹柯先生比较了两者,这自然有其深刻的含义。鲁德斯配得上所有人。除了梵文和塔鲁的个案研究,他还分别在1922年和1930年写了《西域历史与地理》

(《地球与地理》,斯沃,菲尔。-嗨。kl。1922年,第243-261页)和重新讨论西部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嗨。吉隆坡。1930年,第7-64页),利用零碎的出土文献,构建新疆古代历史的宏观叙事。他的主要论文是《印度语言学》(加廷根1940)。我认为陈寅恪受陆德影响最大,他的文献学应该主要是陆德对印度文献学的研究。

《悔罪与杀罪·金光与明经》(1928年6月出版,第一卷,第二号,北平图书馆月刊),其中说:近年来,俄罗斯人c. e .马洛夫获得了突厥语版本的《金光与明经》(1913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第17佛教丛书出版),张犹太进入明朝并与妻子在安固县结婚。还可以看到近年来德国人在吐鲁番获得的吐蕃语残卷,其中有一份残卷与《杀罪明报传》相似。(见a. H. francke,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ai,1924)。《金刚经》几乎是《金刚经》中的第一部,但它太不完整,无法证实。(《第二卷》,第256页)

尹柯先生说,俄罗斯科学院的《佛教丛书》,即沙皇俄国出版的《佛教丛书》,其第十七册是广金·明静(Suvarnaprabhasa)的维吾尔语译本。(《左洛陀布莱斯卡经》)。正如尹柯先生所说,这本书出版于1913年,但实际上出版于1917年。除了维吾尔文字外,尹柯先生还提到了德国远征吐鲁番的收获,即藏文类似于广金明静《明报传》的残本。在这里,他只提示了a. h .弗兰克的名字和发表文章的杂志名称,即“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术会议报告集”(简称spaw),这比文章的标题要少,即“蒂贝提舍·汉斯克里提芬得·奥斯图潘”,SPAW,1924年,第三期,第5-10页。这里出版的藏文“故事”片段是尹柯先生的《鬼报传》。弗兰克是一位长期在西藏传教并研究藏学的摩拉维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解释由斯坦和德国探险队获得的古代西藏文献的人。他的主要作品是《印度西藏古迹》(加尔各答,1926年)。陈寅恪向他学习藏语,所以他对自己的研究很熟悉。

附言还说:“广金明静”是给那些知道它的人,除了梵语。(梵文由萨拉特·钱德拉和鲁道夫出版。霍尔勒,在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手稿遗迹。
本版其余部分,请参阅全芳吉筠《念经梵文·金广明经》,第5卷,宗教研究第3期。其他语言的其他翻译今天仍然可用,而藏语的有三种。(见《日那研究》第4卷第4期《樱布镜》,《蒙古金光明经教科书》)第一部是法成重译的《中国正义网》。有蒙古语和卡尔穆克语的翻译(余增超一份)。满语《大藏经》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应该有《金光明经》,但一直没人看过。突厥语包括由德国吐鲁番代表团(f. w. k. müller,维吾尔语,1908年)和俄罗斯科学院佛教系列获得的残卷。(见上)东伊朗语也有它的根源(见p. peliot,1913年和e. leumann,Abhandlun 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xv,2,1920年)根据各种语言的翻译数量,众所周知,这本书在大乘佛教经典中广泛流传,它是最容易承认其正义的。(第二版第257页,排版的hoernle名称和出版物名称abhandlungen稍有错误。(

在这里,尹柯先生列出了各种语言的《金刚经》。除了传世文献外,还有当时在西域新发现的文献。例如,梵文残卷中有尹柯先生提到的《东突厥斯坦发现的佛教文献手稿残卷》。这本书于1916年在牛津出版,现翻译成图觉·文胤·柯先生引自f. w. k .穆勒于1908年出版的《德国吐鲁番的调查残迹》,这是第一卷(维吾尔语)的第二部分。I-2。APAW,1900年,“佛教徒之死”,最后,尹柯先生不会错过由佩里奥特出版的东伊朗版本。在这里,只提到了佩里奥探险文学系列的语言研究。实际上,它的标题是《伊朗东方的和平》,发表在巴黎语言学会第18卷,1913年,第89-125页。尹柯先生给了洛伊曼一本书一系列的标题:摩根兰德的未来。事实上,我们通常引用这本书的真名,佛教徒、文人、北欧人和德意志人,这本书于1920年在莱比锡出版。除了佩里奥特,这里引用的各种翻译的出版商是梵语、突厥语、维吾尔语和于阗语(所谓的北方雅利安语)时代的学术权威。由此可见,尹柯先生收集了当时中亚地区以多种语言出版的《金广明经》,也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他研究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准备了材料和讨论对象。

敦煌写本《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十诵》(1929年5月刊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5期)。文章中有云:日本西本龙山君影印了敦煌本《普惠尼·鲍罗迪木叉十诵》并附说明,经广泛考证和详细考证。盖皮& # 183;奈耶的优秀比较研究著作。去年,德国的恩斯特·瓦尔德施密德翻译说,有一个梵文“布吕克斯”的残本,适合去柏林参观,我会和他讨论一下。(《第二卷》,第258页)

在这里,尹柯先生联系了在德国出版的梵文版本,根据敦煌版本的西本龙山,日本。所谓的“叶林”应该是对瓦尔德施密德的意译。他是陈寅恪的同学。很可能是尹柯先生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发音和意思都很恰当,姓氏的选择也很地道。不幸的是,它不受欢迎。后来,与他一起学习的季羡林先生称他为“瓦尔德施密特”(《在德国的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40页),华是一个全才。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接管了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资料后,其才能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他与探险队员莱克克合作研究西域佛教艺术,完成了1922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的《密特林佛教史》七卷本,包括龟兹壁画的考证和编年;此外,在1925年,《犍陀罗、库车和吐鲁番:中世纪早期中亚艺术导论》(犍陀罗、库车、吐鲁番。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莱比锡:克林哈特&;比尔曼,1925年);他还与伊朗语言专家兰茨合作研究摩尼教文学。除了上述1926年出版的《易书在摩尼教中的地位》之外,他还于1933年出版了《摩尼教教义与伊朗文本》(Spaw,1933,第480-607页)。然而,大约从1926年起,他的主要业务逐渐集中在中亚出土的梵文手稿上。尹柯先生在这里的翻译表明,有一个梵文“普钦尼·波罗蒂·木叉”的副本,而原来的副本是不完整的。应该是德国IKU的布鲁赫·施特克尔。这时,碰巧尹柯先生正在柏林学习,他和瓦瑟吉有一些交流。因此,瓦瑟吉将学术方向集中在梵文写作上,这也是尹柯感兴趣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从那以后,瓦西成为了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获得的梵文手稿整理工作的骨干和领导者。他出版了大量的文本解读著作,包括大乘经典、小乘经典、阿汗经典等。,并组织了一个团队来编写梵文手抄本《奥斯登·吐鲁番·方丹》,该书根据编号顺序对梵文手稿进行了系统的编目、转录和分发。从1965年到1967年,从那以后,他的弟子们一直在继续工作,最近出版了第十二卷。

这可能是陈寅恪先生回国后最早的研究著作中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有关的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但主要的都在那里,其他的可以通过类比来引用。从这一点来看,先生确实收集了大量研究东方文学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如《语》。事实上,今天从陈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藏》(原东文系)中可以看出,这里有全套的巴厘藏经、拉德洛夫的大量蒙古文碑铭,以及大量的梵文、藏文和突厥文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丰富而现成的,但先生的兴趣明显不同于西方学者,他的目的是对新出土文献进行解读;冯斯塔尔-荷尔斯泰因与他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与他不同的是,他对梵蒂冈的佛经、藏文和中文文本进行了比较;相反,它使用不同语言的文献来解释中国佛经的定义和选择。尹柯先生所做的与其说是对语言学的研究,不如说是对语言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点,请参阅陈怀瑜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七章相关讨论。然而,佛教文献学的基础在于佛经文献学,正因为先生在留学期间打下了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季羡林先生介绍的几十本《学习笔记》(见《纪念陈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使他在翻译佛经汉译时可以举一反三,超越所有的老年人。不幸的是,聚集在清华大学的精英学生和就读于他的学校的优等生都说,尹柯听不懂他的课,也没有人真正跟着他学欧洲正统语言学。20世纪30年代中期,尹柯的学术研究转向以中国为基础的中世纪史,他的文字学和佛教文字学都没有得到“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的支持,直到在海外学习梵语的周一良和同时学习梵语和吐火罗的季羡林回国后,这一摇摇欲坠的学术著作才得以流传下来。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
标题:荣新江:也谈陈寅恪的“语文学”
地址:http://www.02b8.com/yjdyw/24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