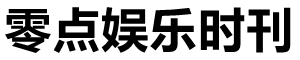本篇文章6842字,读完约17分钟
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蝗虫在2019年开始向世界“进军”,首先使三个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然后越过红海蔓延到中东和南亚,现在威胁到邻国巴基斯坦和印度。
据专家分析,蝗灾不适合中国气候,其传播概率较小,但值得高度警惕。自古以来,蝗灾是中国三大自然灾害之一,是农民最大的敌人和最深的恐惧。控制和消灭蝗虫一直是一个难题和重要任务。一切都如莫言的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所写。为了抗击蝗虫,我们的祖先付出了一切。我们不要求仁慈,也不要求刘猛展示强大的力量。保护老百姓的庄稼是我们的责任。

1927年4月的一天,我爷爷去田里用锄头锄小麦。
从去年秋天开始,在漫长的冬天和荒凉的春天之后,几乎没有下雨或下雪。河水干涸了,池塘见底了,成堆的蝌蚪死在发臭的水坑里。井水落在杆子上。街道布满灰尘。
爷爷肩上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有人问他,关二,你还锄什么?小麦幼苗可能着火了。爷爷说:闲着也不开心,去田里转转吧。爷爷走进自己的麦田时感到沮丧。他看到小麦只有老虎的嘴高,上面有一只苍蝇大小的耳朵。在那之后,爷爷想,大坏收成已经实现了,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了。爷爷对我们说:我们的小麦仍然长得很好,不管它有多大,它仍然有穗。如果它完成了,它可能还覆盖着半桶“蚱蜢屎”。大多数人的小麦是“鸡舍”,甚至没有显示穗。

爷爷站在麦田里,环顾四周,看到三县交界处的广阔土地一片荒凉。往年的这个时候,应该是麦浪滚滚、绿草如茵的时候,但今年的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极度耐旱的茅草和小蚱蜢才会顽强地摘一点绿色。干旱使土地变得碱性,沟渠和荒地变成了银白色,好像下了一层霜。爷爷坐在黑色的土地上,戴上一袋香烟。苦涩的烟呛住了他的眼泪。爷爷的心比那根长香烟还要辣。我拭去眼泪,看见几棵快要枯死的杂草上长满了蚜虫。几只大红蚁背着蚜虫跑来跑去。爷爷挖了一把黑土,用手拿着。他觉得黑土又硬又热,好像是从一个热砖窑里抓来的。

热浪在田野里翻滚,太阳有毒,人们不敢抬头。空万里无云,只有在陆地的远端,似乎有什么东西像烟和雾一样袅袅上升。乌鸦吠叫,听起来像一条裂缝。日子越长,干燥的鸟就越少。几天前,胶州有一群群麻雀随马车低飞,最近几天不见了。村子的井墙上每天都有几只鸟,麻雀和燕子被杀死。为了保持井水的清洁,我们必须用木轮车的花轮盖住井口。现在麻雀不见了,燕子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些黑乌鸦可以陪伴。急切的乌鸦经常从水桶里抓水喝,但是抓水喝的机会不多。他们迷迷糊糊地飞着,有些人飞了又死,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远处响起了枪声,我不知道是谁的军队在和另一支军队战斗。天灾人祸,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所以他们没有心思去关心战争。这一天,爷爷亲眼看到了大量蝗虫出土的奇观。这一奇迹并没有记录在所有的书中。因为我爷爷亲口说的,我相信。

爷爷一生中至少给我们年轻一代讲了100次蝗虫出土的故事。
他拿着一把热黑土,坐在麦田里抽烟。他不经意间低下了头,突然看到一片干燥的土地在他的脚下缓缓升起。他以为自己瞎了,他迅速揉了揉眼睛,但地面仍在缓慢上升。然后,土地像烧过的瓦片一样裂开了,一团暗红色的东西长了出来,形状像一团牛粪。爷爷很困惑。他是一个有丰富农业知识的人,他不知道从地里冒出来什么。他蹲起来仔细看,这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暗红色的牛粪原来是一只像成千上万只蚂蚁一样的小蚱蜢。虽然这些东西很小,但它们拥有一切。腿就是腿,眼睛就是眼睛,它们非常小。三步之外,是一团牛粪在阳光下闪烁着奇怪的光。当你近看时,你会发现你很拥挤,分不清你的身高。爷爷惊恐地看着蚱蜢慢慢地膨胀,好像昙花正在盛开。他惊呆了,不知所措。发现奇迹的兴奋促使他转过头来,寻找一个可以交流和惊叹的人,但是天仇空是广阔的,无人居住。地平线像一条银色的蛇在翻腾。太阳像火一样热,鸟儿在高高的空.军队在远处射击,没人关心出土的蚱蜢。但是我的祖父跳起来喊道:蚱蜢!蚱蜢已经出土了!

爷爷听到膨胀成花椰菜形状的小蚱蜢啪的一声向四面八方飞溅。他们似乎已经学会了在一分钟内跳跃。突然,爷爷的头、脸和裤子上布满了蚱蜢。他们有的跳,有的爬,有的边跳边爬,有的边爬边跳。爷爷的脸发痒,举起手去摸他的脸,他的脸突然变得又粘又腻。

新生的蚱蜢非常脆弱,当它被触摸时会折断。他们的身体遍布爷爷的手和脸。爷爷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他拖着锄头,匆匆走出麦田。他看到在小麦垄之间,东边有一簇,西边有一簇,都是暗红色的蚱蜢群,像牛粪和蘑菇,从干燥的地面上突出来。当它们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炸。在四周的爆炸声中,低矮的稻草和黑色的草地上有爬行的蚱蜢。爷爷的指甲上粘着一只小蚱蜢,好像故意让他欣赏。爷爷仔细观察它,发现暗红色的小精灵长得非常精巧。它是如此的小、精致和复杂。只有上帝能做这样的事!爷爷浑身发痒。首先,他摸了摸肩膀,擦了擦后背,然后跳了起来。在他的心里,他既激动又害怕,好像他绝望了。虽然没有人在附近或远,他又喊道:

出土!出土了!蚱蜢神出土了!
爷爷带回村子的消息让村民们更加紧张。那时,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人。现在有人跑到田里去看发生了什么。我父亲告诉我们他也去看了。那年他只有五岁,只有一点记忆。他们没有看到蚱蜢发掘出的奇迹。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被干旱折磨致死的田野,突然在耀眼的阳光下变得生机勃勃。蚱蜢在所有的不死植物上跳跃,细小但极其密集的叮当声在广阔的土地上滚动。每个观看它的人都感到发痒和眼花缭乱,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我父亲在田里看完蝗虫回来,看见他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正在主屋摆香桌。两支蜡烛是三炷香,烛火跳跃,香烟缭绕,鬼气袭人。奶奶跪在香案前,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磕头。奶奶说蚱蜢是帝王的虫子,是玉帝养的。创作者在“黄”一词旁加上“虫”一词,便成了蝗蝻。蝗虫是帝王虫,帝王虫是蚱蜢,翻过来也是如此。

几天后,东南风刮得很大,乌云滚滚而来。空的空气变得潮湿,村子前面的池塘在晚上散发出恶臭。被褥粘粘的,跳蚤猖獗,爷爷很难入睡。他告诉我们那一年一切都不正常,人们总是觉得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蚱蜢出土后,田野是白色的,连坚硬的草棍都被吃掉了。那些小神的嘴真的很好。爷爷说前几天,村里有些人去木瓜寺烧香磕头,求他们发发慈悲。事实证明,这种活动是无用的,他们一点也不欣赏它。男人们不在乎女人们的迷信活动,他们知道田野里已经没有东西留给神虫吃了。他们不能吃土壤和人。吃光你能吃的东西,它们就会迁移。

有了东南风,人们有希望,但也有忧虑。我希望我们能下一场雨,种下秋苗。令人担忧的是,吃了所有草茎的蝗虫不愿离开,仿佛在等着吃秋苗。
爷爷睡不着,所以他在院子里踱步。东南风吹在人们的胸口,碎纸在他身后响着。雨来了,真的来了。尽管有蝗虫的存在,遭受旱灾的村民们仍然非常兴奋。雨越来越近了,地平线上已经有了晃动的闪电。爷爷知道开枪的不是士兵,而是雷公握着的那把破扇子。爷爷暗暗祈祷:希望田师傅能在下一场暴雨中打杀这些害虫,同时解决土地干旱的问题。

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夹杂着冰雹和杏仁。村民们欢欣鼓舞,感谢上帝不仅解决了干旱,还消灭了害虫。但是天亮后,我去了田野,发现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雨和冰雹确实杀死了一些蝗虫,但是更多的蝗虫正在旺盛地生长。在雨后的日子里,它们的身体变得与大花生相似。充满雨水的地球为经历了冬天和春天的植物提供了极好的生长机会。所有的植物都长出新叶,所有的种子都破土发芽。然而,所有新种植的东西都成了蝗虫的美餐。他们从不挑食,也不怕中毒。不管是有奇怪气味的薄荷还是有有毒气味的马钱子,只要它从地里出来,他们就会把它嚼干净。蝗虫的气味也毒化了空毒气,粉碎了人们的勇气。

雨后,大地仍然光秃秃的,绿叶不足以填满蚱蜢的牙齿。植物很生气。去你妈的。我们不会长大。看你怎么吃。如果你有能力,你就会变成拉拉咕,钻到我们的根部吃掉。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出去就不会出去,蝗虫有点不安。他们不安分的表现是他们从田野搬到了村庄。他们爬上墙,来到房子前,吃光树上的新叶子,开始啃树皮。据传,丰村李达家的小儿子被蝗虫咬了。爷爷对这个问题持否定态度。他说:蝗虫真的很凶猛,但是它们还没有凶猛到可以咬人的耳朵。

村头的帕瓦克斯庙和村后的刘猛将军庙的熏香再次繁荣起来。
据爷爷说,木瓜寺的神是一只像小驴一样的大蚱蜢,有着奇怪的形象,一个头和一个蚱蜢的身体,令人生畏。刘猛是刘猛将军庙的自然神。我查了一下资料,得知刘猛是元代吴川人。他曾经下过命令,带领军队消灭了江淮地区的盗贼,并在一艘船上取得了胜利,这与蝗灾和穷人相吻合。刘猛带领队伍去消灭蝗虫,但是蝗虫被杀得越多,他就越愤怒地扑到河里。晁时的一个师,被授予刘猛将军的职位,并被列为神的职位,专门负责为人民驱蝗。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矛盾:既然蝗虫是玉帝饲养的家养昆虫,在刘猛杀昆虫不是一种祸害吗?如何授予他爵士头衔?还不清楚。让我们离他远点。我们还是谈谈蝗虫吧。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手软手硬。有时用一只手,有时用软的和硬的。

刘猛将军雕像
在我们村子里对付蝗虫的方法是令人宽慰的。首先,他们在木瓜寺烧香磕头,献草药,看着无效。然后他们去各个家庭筹集一些钱,在村子里搭起一个舞台,并邀请一个蚱蜢队为蚱蜢表演三部戏剧。说这是蝗虫的游戏,但实际上是人的游戏。我父亲是那三部戏剧中最热情的观众。几十年后,他仍然记得那天的情景。他说三部主要的戏剧是:“放粮”、“捉放曹”和“五家坡”。我父亲告诉我们,当表演盛大时,四个镇的人都来剧院,观众挤满了人。孩子们的印象总是被放大。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聚集一大群人。在我的想象中,60年前《蝗虫》的表演大概是这样的:在空荒芜的叶原,搭建了一个低矮的土平台,几个人穿着油脂和粉末在平台上移动,几个无聊的游手好闲的人坐在或站在舞台下面,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我是头上有一个。在表演过程中,蝗虫跳到舞台上,跳到演员的脸上,有些甚至跳到演员的嘴里,这样他们就不能张嘴唱歌剧了。

也许是人民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它的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齐心协力吃掉了我们东北高密乡,因为“广袤的白色土地真的很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徙了。这是另一个奇迹。我的祖父不是唯一一个看到这个奇迹的人。村子里的十几个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告诉过我蝗虫过河的事。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条蛟河,我们村子前面有一条顺溪河。如果蝗虫想迁徙,它们必须穿过这两条河。大雨过后,河里有半个人深的水。当时蝗虫大约有三厘米长,巨大的头部和背上的两个“小包袱”(发育中的翅膀),正处于愚蠢和丑陋的跳跃阶段。让我们听听他们是如何过河的。

据说那天,村民们站在河边看着蝗虫过河。人们首先听到田野里的低噪音,然后他们看到田野在抽搐。泥泞的蝗虫群在光秃秃的土地上翻滚。蝗虫形成波浪,一个接一个,涌向河边。孩子们害怕大人们看不见他们,大声喊道:来,来,蚱蜢神来了!这时,河水滚滚,碧蓝如水;河的外面是汹涌的蝗虫和红色的波浪。大人们看着蚱蜢追逐河岸的长长的波浪,它们的脸像泥土一样。萨萨萨萨萨,沙沙溢...一批接一批,一列接一列,数万匹马压着数千匹马,层层叠叠,层出不穷。爷爷带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说:“如果蝗虫吃土壤,吃河岸也不难。

引起这场蝗灾的沙漠蝗虫已经飞过红海
当时,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的《战火纷飞》中到处都是弹孔;官僚们混水摸鱼,收受贿赂和欺骗,缴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土匪猖獗,士兵陷入困境,流行病肆虐;人们在困境中挣扎。
蝗虫像长龙一样在河里翻滚。这条河原本像蓝色缎子,现在布满了洞。河水充满了色彩,浑浊的波浪正在上涨。他们在每个人的密切注视下靠近对岸,然后突然分散成千千数千个人,并突然改变对岸河岸的颜色。最终,他们消失在广阔的袁野另一边。他们长吁了一口气,心中像一块石头掉到了地上,但同时又感到失落。

下午,爷爷去地里播种。
半个月后,绿色的幼苗在地上披上一层薄薄的绿色外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天气会如你所愿,天气会很好。在古代历法的七月,高密东北乡的广阔土地变成了绿色的海洋。虽然小麦季节没有粮食丰收,但只要不出意外,秋收就足以解决人们一年两个月咀嚼粮食的问题。

没有人敢乐观。春天,蛟河对岸蝗虫留下的巨大阴影总是笼罩着空.高密东北乡就像石头一样,蝗虫的恐怖压迫着人们的心,当然也压迫着我祖父的心。
这是注定的。
蝗虫卷土重来的日子是农历八月初九。那天阳光很好。空的天空非常蓝,有许多鸟。满坡上的高粱已经被大米染红了。秋风吹来,高粱像海浪一样前呼后拥。爷爷用木制独轮车把肥料运到地里,推了几车肥料,已经快中午了。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拉车的黑驴也横冲直撞,不听招呼,好像被什么野兽吓着了。木制手推车在驴子的斜拉下倒塌了。爷爷扔掉车把,挥舞着鞭子,正要给驴子一个教训。突然,他看到一团深红色的厚云从空.的西北天空飘来爷爷心中一惊,手中的旗杆掉到了地上。一瞬间,红云飞到了空村,并迅速转移到了田野空.爷爷听到红云中一声裂纹,像盔甲摩擦的声音。那朵红云转了一会儿,好像在进行地面侦察,然后突然爆炸了。一天,黄色的雨,数以千计的金星和箭落在地上。我们面前的一切,红高粱、金黄色的麦穗和绿色的树木,都变成了粗糙的红棕色。十几个农民慌慌张张地跑着,边跑边惊恐地喊:“回来...蚱蜢神回来了……”

爷爷一动不动地站着,像一棵枯树一样多年。两行泪水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第一批是先头部队,当他们登陆时,大量的蝗虫不断地飞进来。空的天空中,毛茸茸的云团翻滚着,无数的翅膀扇动着,发出可怕的声音。空的天空是暗淡的,太阳被遮住了,就像末日一样。

村民们被震惊了,他们跑向自己的庄稼,敲打着铜锅和瓦片,挥舞着扫帚,大声叫喊,希望蝗虫会害怕,不会在这里着陆。但是蝗虫一点也不害怕,它们仍然到处飞来飞去。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它们的背上长出了翅膀和羽毛,它们的后腿也变得强壮了。春天柔软的四肢现在似乎是从铁皮上切下来的。他们疯狂地咀嚼着,田野里响起了雨声,庄稼长满了坡,丰收在望,转眼间消失了。

爷爷说:春天他们在肚子里吃饭;现在他们不吃东西,他们只是咬,如果他们咬,他们就完了。前者是为了生存,而后者似乎是被故意摧毁的。看到飞蝗之后,我回想起春天的跳跃,却发现它们真的很温柔善良。
天黑得太早了,大批蝗虫也从西北方向增援。他们有多少军队?它似乎永远不会耗尽。偶尔,一缕红色的阳光从厚厚的蝗云中射下来,照在精疲力竭、声音嘶哑的人们身上。脸是绿色和黄色的,关怀是暗淡的。即使在红色的灯光下,玉宇里也有星星像蝗虫一样闪烁。

夜幕降临后,田野有节奏地滚动着,发出巨大的噪音,仿佛有一百万军队在操练。人们关上门和窗户,躲在房子里,焦急地坐着,甚至连孩子都害怕睡着。人们听着田野和冰雹蝗虫敲打屋顶的声音。村子里的树枝裂开了,被蝗虫压碎了。

第二天,人们艰难地推开门,看到村子里布满了蝗虫。绿色不存在,甚至屋檐上的干草也被啃掉了。蝗虫充满天地,成为万物的主宰。
既然他们已经吃光了所有可食用的东西,村民们就不害怕了。你不能吃人吗?!在爷爷的号召下,村民们被动员起来抗击蝗虫。他们挥舞铁锹、扫帚、棍子、铲子、拍击、清扫和滚球。他们打得越多,就越愤怒。啃食草木的蚱蜢充满了毁灭的喜悦;村民们杀蝗虫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复仇的喜悦。

爷爷说村子里有一个叫吴娈的人,他在村子的头上点了一个草堆。烟柱在飞升,与蝗虫相连;火焰熊熊燃烧,蝗虫纷纷落下。村民们通过增加木柴和工资来增加火势。当木柴烧完时,木头被扔进去,当木头被扔出来时,房子的门板被移走。为了抗击蝗虫,我们的祖先付出了一切。我们不要求仁慈,也不要求刘猛展示强大的力量。保护老百姓的庄稼是我们的责任。

清代捕蝗图
十天之后,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突然,到处的蚱蜢都消失了。他们去哪里了?没人知道。只有光秃秃的树和坚硬的植物根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蝗虫,这种小型节肢动物,能用一只脚把一堆小东西扭死。一旦他们形成一个群体,他们就能产生如此巨大而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有摧毁一切和毁灭一切的潜力。自称万物之灵的人在他们面前是无助的。这里隐藏着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

蝗虫,一种肮脏的昆虫,总是与饱受战争蹂躏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仿佛它是乱世的生动象征。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
1927年,东北高密镇的蝗灾给祖父们带来了灾难,但也给世界留下了惨淡的印象。祖父母只看到了他们头顶上空的一个小日子。事实上,今年,蝗虫像飓风一样席卷山东大地,并蔓延到河北、河南和安徽省,受灾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受害者数百万。我对我的祖父们所目睹的感到惊讶,更令人惊讶的是我的祖父们没有看到。据一位在吉焦铁路当火车司机的老人说,那年蝗虫像小山一样落在铁路上,挡住了火车的去路,吉焦铁路的交通中断了72小时。

我们只能想象这惊人的一幕。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
标题:莫言:那一年,我老家高密东北乡的蝗灾
地址:http://www.02b8.com/yjdyw/247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