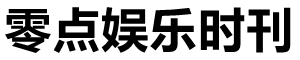本篇文章8160字,读完约20分钟
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以前,即20岁以前,他在中国留学(虽然他去日本的时间很短),这是陈寅恪学术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20岁以后,先后留学瑞士、法国、美国和德国,其中留学时间最长的是德国柏林大学,这是陈寅恪先生学术道路的第二个阶段,是学习西学的阶段,也是陈寅恪成为陈寅恪的关键时期。1926年后,陈先生赴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陈寅恪学术发展道路的第三个阶段,即中西学术融合的创造性阶段。目前,陈寅恪研究中最不清楚的是他的留学生活。引用最多的文章是余大伟和毛子水的感伤回忆。

1969年,陈寅恪先生逃到道山不久,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名伟在《东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说陈之死使我们失去了本世纪他那一代最有学问的学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集》于1971年出版了第三辑陈寅恪先生散文集《余大为先生散文集序》,汉堡大学汉语言文化系教授刘茂才出版了《陈寅恪先生散文集》书评,称赞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范围之广[②]。陈寅恪是如何获得如此广博的语言和学科知识的?刘茂才教授的书评提到了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的一些老师。除了lueders,还有erih haenisch,f.k.w.mueller,erih hauer,otto franke等等。这些学者是印度系、汉学系和柏林民俗博物馆的教授或东方学家。摘要:本文根据笔者在柏林考察的一些资料,对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柏林学术界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以期为陈寅恪的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一、关于陈寅恪先生在德国留学的情况
刘贵生教授在《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德国学习资料的抢劫与残迹》一文中介绍了陈寅恪先生在德国学习的一些基本资料[③]。1997年8月我访问柏林时,也发现了一些材料。除了刘娇寿文章中介绍的材料外,主要是陈先生每学年的学期登记表,如陈先生住在康德街30号。在1921/1922年的冬季学期和1922年的夏季学期,搬到了第22号Kona Zeebek Str。1924年夏季学期。我很想了解一下陈寅恪先生那一年所学课程的情况,发现有些学生的毕业证书中包含了他们所学的课程。例如,于大伟先生的毕业证书记录了他曾经上过一门物理课。然而,陈先生的毕业证书上没有任何参加课程的记录。根据笔者对洪堡大学档案馆管理员的查询,可知1924年以后毕业的学生的档案还有其他的管理方法,即学生所选的课程记录在其他材料上,而不是毕业证书的档案上,这些材料由于被战争破坏而无法找到,这使我们无法了解陈寅恪先生当年所选课程的具体情况和学分。据记载,陈先生于1921年11月3日入学,1925年12月17日退学[④]。在离校材料中,仅发现陈先生被派出所传唤的一份记录。档案管理员告诉我,外国学生经常有户籍或其他问题,需要去警察局。

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的报名表上写的是哲学专业,但在1921年至1925年的每个学期的报名表上都写了梵文(刘娇寿介绍的第112卷除外)。这是因为当时印度学、汉学等学科都属于哲学类院校,这并不意味着陈先生一开始申请的是哲学专业,后来转学梵文专业,所以有些形式上标明了梵文/(Phil)。),意思是“梵语(哲学学院)”。

二。柏林大学课程开发
德国柏林大学于1810年正式成立。创始人和首任校长威廉·洪堡特(Wilhelm humboldt)推出了一项新的以科学研究为重点的办学政策。从现代意义上讲,西方大学制度实际上是从德国的柏林大学开始的,或者说,从中世纪教会学校中诞生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只有在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dt)建立了柏林大学之后,才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型大学。20世纪20年代柏林大学的课程设置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除了各个系的专业课程外,大学里还有一些跨学科的公共文化课程,其中的“中国宗教”、“中国哲学”和“东方伦理学”与陈的兴趣有关。此外,德国大学还有几十门免费的选修语言课程。除了现代欧洲语言,如英语、法语和俄语,还有各种现代东方语言和古代语言。这为陈寅恪先生学习各种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

1988年在广州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季羡林教授为我们讲解了陈寅恪先生的64本笔记的内容。它涉及藏语、蒙古语、梵语、巴利文和其他语言,当时柏林大学提供这些语言。从笔记本的内容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关于陈寅恪先生所选课程的笔记。德国柏林大学的语言课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语言课程,另一类是阅读练习课程。前者一般是学习语音、语法和词汇;后者一般是阅读理解的训练。

陈先生笔记本的第8版,在13个藏文版本中,封面上写着“藏文一号”,显示了藏文字母和风格的变化,第12版也显示了藏文语法。第九本书的封面上写着“藏文二号”,其中复制了藏文的句子和单词。这是陈寅恪先生学习藏语的笔记本。练习课要求阅读原文。一般来说,有些文件是根据不同程度选择的,阅读和理解原文的能力是通过翻译实践来培养的。第10、11本藏文笔记本为藏文文档,部分以中文、英文和德文标注,应作为阅读练习课(≤ übung)的课堂预习笔记。藏文2号、3号、4号、5号和6号笔记本是藏传佛教经典或铭文,其中一些有英文翻译,也应作为阅读练习课的笔记本使用。

蒙古语的第二个笔记本是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字、名词格、介词等。西方蒙古语,以及蒙语词汇等。,这应该作为基本语言类的注释。这本书的第五页是从古蒙古语抄来的,应该作为阅读练习课的笔记。众所周知,当时柏林大学的海涅斯教授开设了蒙古官方文件选编等课程。陈寅恪用其他语言记笔记可以类推。

由于这些课程是自由选择的,即使是那些攻读学位的人也不需要学习,甚至不需要学分。是否参加考试完全是我自愿的,甚至课程的时间都可以提前约定,所以这很合陈先生的口味。例如,在1924/1925年的冬季学期,艾伯特·赫尔曼博士开设了两门课程:“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和“13世纪以前的中国游记”,没有给出具体的上课时间和地点,但根据选修课的情况,上课时间是事先单独商定的[6]。

陈寅恪先生的笔记中也有大量的书目。我想这是柏林大学另一类课程的学习笔记——研讨会。在讨论课上,老师通常会给出大量的讨论主题和大量的参考书目。参与者阅读相关书籍和文件,撰写口头和书面阅读报告,并进行讨论。当时没有复印设备,所以学生们不得不把老师给的书目抄在笔记本上。事实证明,《蒙古文》第一册中的各种书目都是偶数。《藏文》第一版用德文写着“柏林的甘珠尔”和“圣彼得堡的甘珠尔”,这可能是讨论课的内容,还有一张1924年9月8日的借书单(当时还是暑假),陈寅恪先生可能用它来准备下学期的讨论课。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曾偶尔翻开这些读书笔记,或许是想起他留学期间的艰辛,发出一声悲叹沧桑。

三。柏林大学印度系和陆德斯对陈寅恪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去柏林大学学习印度研究,主要是梵蒂冈语言和文学。柏林大学的印度研究是什么样的?
柏林大学的印度研究专业成立于1821年。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梵语学者威廉·洪堡特(wilhelm humboldt)是普鲁士政府的教育部长,也是柏林大学的校长,他聘请了在巴黎任教的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作为该学科的第一任教授(工作时间1821-1856)。鲍勃因五年前发表的《论梵语的同义系统:与希腊、拉丁、波斯和日耳曼的同义系统的比较》而闻名于世,是比较历史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鲍勃被阿尔布雷特·韦伯(1856-1902)取代。韦伯的继任者是皮埃舍尔(1849-1908,工作时间1902-1908)。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德国许多著名的印度学者,如季羡林先生的日尔曼语教师埃米尔·西格(emil sieg)和卡尔·盖尔德内尔(Karl f . geld ner),都出生在柏林(Sike于1896年完成了他的教授论文)。从这里,一位梵文教授走了出来,并担任哈勒大学、基尔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其他重要的印度研究城市的主席。

本世纪初,柏林赋予印度研究新的历史使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学者是皮埃舍尔教授。19世纪末,斯文·赫定在中国新疆的考古调查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01年,斯坦因在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研究会议上报告了他受印度殖民政府委托研究中国西部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02年,皮埃舍尔出任柏林大学印度研究教授,积极推动中亚考古工作。他组织成立了吐鲁番委员会,并担任负责人,因此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负责人格伦·魏德尔和勒·科克先后四次出访吐鲁番。从那以后,皮埃舍尔发表了关于吐鲁番梵文文献的研究论文。

吐鲁番探险队带回的手稿和印刷材料有17种不同的语言和24种不同的语言。其中,最丰富的是伊朗和突厥文学,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佛教文学中发现了一种印度-日耳曼语言——吐火罗语,这在过去是完全不为人知的,而柏林的两位印度学者锡克和威廉·西格林是这种语言的发现者和破译者。

皮埃舍尔于1908年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他的继任者是陈寅恪的著名老师鲁德斯(1869-1943)。鲁德斯毕业于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与著名的埃及古物学家和语法学家基尔霍恩完成了他的论文[8]。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在搬到柏林之前,他是罗斯托克大学和基尔大学的教授。后来,柏林的印度学术界评论道:陆德斯在柏林大学33年的非凡成就表明,邀请这位40岁的学者担任柏林世界级的印度研究讲座是哲学学院的明智决定。

至于陆德的学术特点,他的亲信弟子阿尔斯多夫评论说:陆德也许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个不能用“印度学者”来概括的学者。人们不知道他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专攻什么领域。他是吠陀文献学最伟大的老师之一,他一直把吠陀研究作为印度研究的中心内容。他也是最有成就的墓志铭和古代文献学家,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献是他最专注和杰出的领域之一。陆德斯还编辑出版了《德藏吐鲁番文书》(未竟事业后来由他的学生瓦尔德施密特、季羡林先生的博士生导师等完成。)。他还留下了无数未发表的手稿。鲁德斯是正直的,纳粹政权试图利用他的名声为法西斯政治服务。1935年,他毅然悄然退休,1943年去世后,他再也没有去柏林大学讲课。

鲁德斯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印度学者。其中一位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是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1897-1985),季羡林先生的老师。从1918年到1919年,沃恩在基尔大学学习锡克教的印度研究。第二年,锡克教徒去哥廷根大学教书,瓦舍姆去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印度研究,包括汉学和藏学。他的老师是鲁德斯、威廉·舒尔茨和法兰。1924年从博士毕业后,鲁德斯建议他的学生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印度部担任勒科克的助理,研究中亚考古学,尤其是吐鲁番文学。自那以后,瓦尔德施密特一生致力于研究西域宗教和吐鲁番文献,编辑出版了《吐鲁番发现梵文丛书》[10]。事实上,华西和陈寅恪年龄基本相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受雇于陆德的同学。鲁德斯也有一些外国学生,除了陈寅恪,还有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在这里,我想回到陈寅恪先生的笔记本上说几句话。共有10个笔记本“梵文、巴利文和耆那教”,其中第三个题为“梵文大困境”,是古代印度语法学家帕塔贾里写的mahābhāsya,是一个英文译本。鲁德斯是这部经典的权威学者。第五、第六、第七碑文是石刻,这是陆德斯科学研究的力量。4号、8号、9号和10号是巴厘岛人的词汇书,是陆德最重要的研究领域。第14版笔记本《突厥回鹘A班》中有几个教授的名字,其中有一个陆德的名字,说明陈先生确实听过他的课[11]。我们无法确切证明陈寅恪先生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但从陆德先生上述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兴趣,以佛教文学为中心的研究特点和他的政治操守,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先生的影响。

四。米勒和其他柏林学者[/s2/]
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穆勒(1863-1931)是陈寅恪先生在柏林求学期间的另一位老师。米勒于1883年进入柏林大学神学系。当时,所有研究神学的人也都研究过东方主义,但像米勒一样同时研究汉语的人并不多。他的语文老师是著名的汉学先驱威廉·格鲁布。后来,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并于1889年获得博士学位。冯·加伦茨是他的导师之一。

米勒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在柏林的富尔·沃克斯昆登博物馆兼职,并担任格鲁伯的助理。毕业后,他继续在这里的东亚部工作。当时东亚部的负责人是顾鲁波,印度部的负责人是格伦·韦德尔。后来,米勒接替顾禄波担任助理馆长,主管东亚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有机会去远东旅行。回到中国后不久,他担任馆长。因此,在陈寅恪留学柏林期间,米勒担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在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像往常一样被授予教授的头衔。

米勒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除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其他东方语言之外,他还对马来语和暹罗语等印度支那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论文还包括吐鲁番佛教文献、开封犹太教堂和西方语言、文献、历史和宗教,如维吾尔语和粟特语。魏勒和沈德勒说:“在德国,甚至在整个东方学术界,都没有像米勒那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12]米勒在柏林大学开设课程,例如在1924/1925年冬季学期教授“吐鲁番发现的佛教文献”。

陈寅恪在德国期间,柏林大学的汉学家主要是奥托·弗兰克(1923-1931)和埃里希·海尼斯奇(1921-1923年代理教授)。作者在一篇专门的文章[13]中介绍了富兰馆的情况,这里不再详细讨论。1899年,轩尼诗在柏林大学学习汉学、蒙古学和满洲学,还学习印度学和其他东方学科。他于190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13年通过了教学论文。他的论文充分利用了汉语、满语和蒙古语的材料。1920年,柏林大学汉学系新设满蒙研究教授一职,由海尼斯担任。汉学系教授高燕于1921年逝世。直到1923年富朗格上任,他一直担任教授。我们在1922年夏季学期的课程表中找到了海涅斯写的《满语语法》,时间是每周五中午12点到中午1点;蒙古文选读,每周四上午9: 00至11: 00。在同一个学期,米勒教授中国佛教文学,埃里希·施密特教授中国宗教哲学。

海涅斯在学术界以研究蒙古史而闻名,他的同事埃里希·豪尔(1878-1936)擅长于满族研究。1921年从柏林大学毕业后,霍尔还教授满语语法和精选阅读课程。他的主要著作有《满蒙语法学》和《满汉语法》。傅兰格、轩尼诗和霍尔曾与西藏学者弗兰克合作,研究洛弗尔从北京获得的汉蒙满藏四言板。这种学术氛围无疑对陈寅恪的学术旨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后来所说的“前流”不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潮流,而是包括柏林学术界在内的欧洲东方学术界的潮流。

从陈先生后来的学术实践来看,他受到了柏林学术界的影响
那么陈先生自己是如何“预流”的呢?
于大伟曾以《蒙古秘史》为例,说明陈寅恪先生是我国第三代治蒙古、治袁史的代表人物:第一代发现了《蒙古秘史》,但不了解蒙古文;第二代使用欧洲翻译来补充元朝的历史事实,但不了解西方语言。第三代学者“开始研究中国西北和中亚的文字,并能直接阅读蒙古史的资料”[15]。陈寅恪先生研究蒙古秘史、蒙古文字和西文的老师是以研究蒙古秘史和元史而闻名的海尼斯教授。回国后,陈先生发表了《蒙古源流考》等一系列文章。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任教时开设的课程有《西方人的东方主义目录》和《梵文语法》等。指导学生学习论文的领域有“古代碑铭与外国民族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维吾尔语翻译的比较研究”、“蒙古满书与历史相关文献的研究”等。根据蒋天舒教授主编的《陈寅恪先生年谱》,自1927年以来,陈寅恪先生先后在《国学》发表了《大乘·米·钱景与倾听与勤奋》和《有情人的一生与命运》;在《清华学报》上,他发表了《儿童遭受隐喻之苦,梵文残跋》;在《北平图书馆月刊》上发表了《忏悔与除罪》、《金光与明朝》、《明朝》等文章;后来,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杂志》上发表了《几何满文译本后记》等文章。显然,陈寅恪先生的教学内容和研究课题基本上不属于佛教、梵学、蒙古学和满族学的范畴,这意味着他的研究兴趣与柏林汉学家和印度学者相同。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期间,刻苦钻研中国佛经,所以同时研究隋唐历史。1935年,他把金介绍给[16]。因此,自那以后,关于隋唐史的著作越来越多,但关于梵蒂冈研究和西北历史地理的论文却越来越少。重要原因是这种学习是当时欧洲东方学术界的“潮流”,而不是中国学术界的潮流,“前流”不容易,所以它是高的和低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外很难看到新的研究成果,而中国没有条件继续进行这种研究,所以陈先生不得不放弃他的专业领域,转到中世纪[17]。可见,有人说陈寅恪先生是国学大师,这不是陈先生的本意。王先生的初衷是致力于西学——研究西域的历史和地理(即所谓的西学东渐),他的志向和基础是在柏林求学期间形成的。

陈寅恪先生回国后立即闻名于世,主要是因为他在西域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造诣,以及他在学术领域发表的无人敢涉足的论文。这种学术领域是国际东方学术界的“潮流”。几乎只有陈寅恪是中国合格的先行者。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和应用给了中国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发言权,但只有那些掌握了西方学者所掌握的语言知识的人,才有能力与西方学者交谈。当时,在中国几乎只有陈寅恪是合格的对话者。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肆虐的“西学东渐”中,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家学渊源的陈寅恪受到了中国传统学术界的推崇甚至崇拜(如陈寅恪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邓广明的《宋史正史考证》);郑天挺说,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传说梁启超向清华研究院推荐陈寅恪的感谢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陈寅恪的先驱作用也影响了季羡林、韩儒林、周一良等后来者的海外求学之路。

(本文收录于《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也发表在《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第86-94页。(
[①] t'oung pao,第57卷,1971年,第136-143页。
[②] oriens extremus,jg.19,1972,s.119-125。
[③]《北京大学史》,1977年第4期,第308-316页。
[④]参见柏林洪堡大学档案馆,第2019/112号,第112页。
[⑤]季羡林:《从学习笔记看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范围和学术方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7页,第79页。
[⑥]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ait zu Berlin,verzeichnis der vorlesungen,1924/25ws,s.9 .
[7]关于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情况,参见杨《德藏西域梵文: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第127-138页;容新疆:《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知识与记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92页。
[8]陈寅恪先生的笔记本《天台梵天》抄录了基尔霍夫的考证文章,谈及天台梵天的来源和内容。他就是这个基尔霍恩。
⑨《柏林的吲哚洛基:1821—1945》,载于《柏林研究》,1960年,第567—580页。
[⑩] "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zdmg,vol.132,1987,s.8—11。
[11]季羡林:《从学习笔记看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87页,第79页。
[12] "f.w.k.mueller ",asia major,no.1,1933,s .ⅶ-xⅵ。
[13]萧潇著:《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奥托·法兰传》,载李学勤《国际汉学行走》(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865页。
[14]参见我的书《德国汉学》,中华书局,1994年,第73页。
[15]蒋天舒:《陈寅恪先生年谱》(增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页,第93页。
[16]《陈寅恪先生年谱》(增订版),第50页,第93页。
[17]关于陈寅恪研究重心的转变,参见桑冰《陈寅恪与清华国学》,《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张国钢
来源:零点娱乐时刊
标题: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
地址:http://www.02b8.com/yjdyw/24677.html